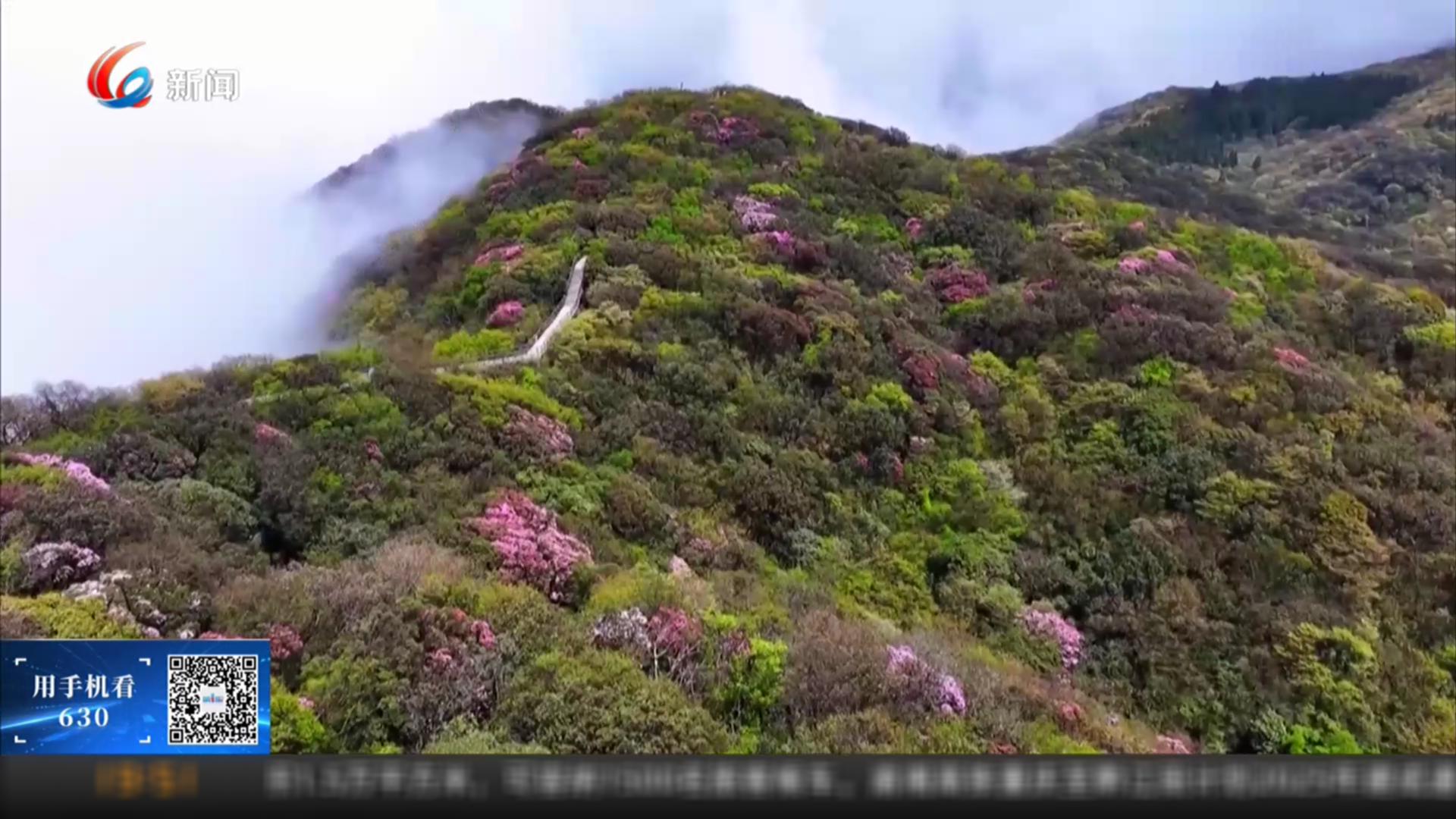豫才先生在《野草题辞》中写道:“天地有如此静穆,我将不能大笑而且歌唱。天地即不如此静穆,我或者也将不能。我以这一丛野草,在明与暗,生与死,过去与未来之际,献于友与仇,人与兽,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。”这大概是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了,于野草之喻中代表着华胄而洁歌。可鲁迅先生不只直接呐喊,不只将丰沛情感径自流露,也不止于诗。
《祝福》来自鲁迅先生的小说集《彷徨》。如果说《野草》是一江肆意奔向远方的春水,那么《祝福》则为一汪深不可测灰黑的海洋。自我意识的寻找在《祝福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,在课本节选的片段里看似“我”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物,未起到什么举足轻重的作用,全篇只是以“我”的视角来叙述整体故事。但真正的,在《祝福》这篇万余字的小说中,与“我”相关的篇幅就高达四千多字。
为何鲁迅先生要耗费如此多的笔墨来塑造“我”呢?我们不妨将视线聚焦于“我”的作用此方面上来。我此时还未提到“我”的动作和语言,只是以为,上述两方面都是为“我”的作用服务的。而说到语言,便也分为文中“我”人物的语言和鲁迅先生塑造“我”的文字语言。
我身上汇集了当时鲁镇这样一个小圈子的意志,但影射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意志。且,由我反映了作者处于历史文化动荡和碰撞中的主体意识或精神特征——对人“生”与“死”的永恒命题的关注。这恰恰是鲁迅先生创作中常提的主题,这便又要让我们提到《野草》了,鲁迅先生在野草题词中多次强调生命的死亡与腐朽,并以野草作比,还表现出他“我将大笑,我将歌唱”的释然。在文章中,此对于生死之思考由鲁迅先生自然精湛的语言所体现。祥林嫂问:“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?”祥林嫂期待着知识者能够给予她权威的回答,赋予她面对死亡的信心和重见家人的自信。这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到“我”的回答与反应。我像在学校里遇到“不及豫防的临时考”“在极短的踌躇中疑惑了”“吞吞吐吐地说,也许有罢——我想”,鲁迅先生用“我”的语言和动作展现了知识者在道德与真理之中的徘徊。犹豫着是否会伤害到祥林嫂,却也思考着人死之后到底有无魂灵的事实。而我的塑造突出了祥林嫂本身也是封建文化的认同者,渴望魂灵赎罪,在自我蒙蔽中寻求暂时的安慰,这何尝不是封建礼教社会的缩影?
我”拥有一种精神意志,正是这种意志驱使着“我”一面在封建礼教社会中匍匐,一面又渴望着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踽踽独行,在逆来顺受中沉默,在沉默中消亡。这更加体现自我意志、人类意志的悲剧性,这是一种不同于卡夫卡《变形计》中的悲剧,这是一种封建礼教社会的悲剧和自我意志的否定。在“我”面对祥林嫂询问之时,结结巴巴,欲言又止,带着科学真理的事实仿佛在唇边被迫止住了脚步,只回答了一句略显敷衍和仓促的话“或许有罢——我想”。至此,我们也许能结合鲁迅先生创作的时间和背景。“五四运动”在1919年发起,而在“五四运动”前后,1915年至1923年,中国正在进行新文化运动,恰巧,鲁迅先生在1924年2月写下了《祝福》,那么我们便可以合理猜测,塑造此知识分子的形象,是否是为了暗示新文化运动的作用,或与鲁四嫂、卫婆子、祥林嫂等人做对比?
但“我”的形象却不是一个彻头彻尾接受过新思想的人,而是一个既具有进步思想,但又软弱无能,屈服于封建礼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。这便体现了鲁迅先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暗示——传播不够深入,不够广泛,没能出现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者。鲁迅先生对此带上了淡淡忧愁与无奈。基于“我”具有进步思想,能通过鲁四爷宅子中的摆设剖析鲁四爷迂腐没落的伪善嘴脸。也基于“我”的软弱无能,文中才会出现“无论如何,我明天决计走了”,以逃避现实,自我欺骗。这里还要提到鲁迅先生启蒙主义小说中的双声复调意义结构,落脚于对启蒙话语的言说和对启蒙话语的拷问,从揭示下层社会病苦转移到剖析启蒙主体自身的精神弱点上来。鲁迅先生希望通过呐喊和文字唤醒民众,自我疗救。
《祝福》中的“我”,我以“人类的意志”诠释,“不要让别人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。当灾难来临,人类的精神意志才是第一序列。”